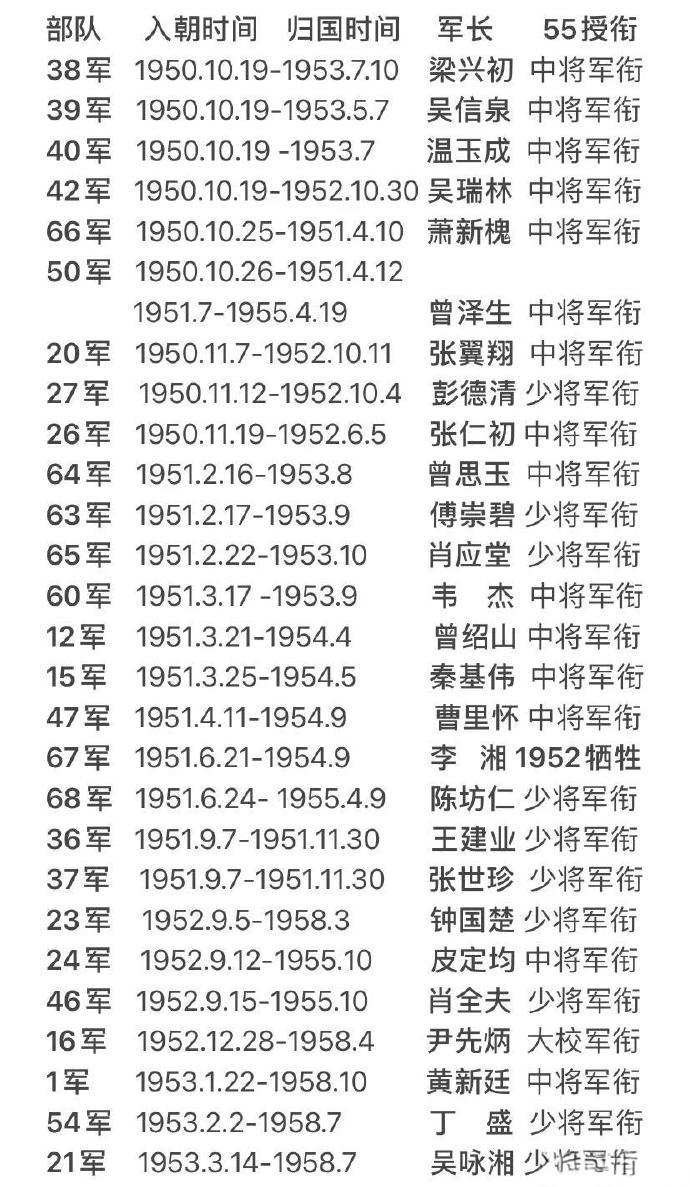上甘岭战役志愿军45师烈士遗照一一照片由原志愿军45师前线指挥所秘书谢万丁捐献
上甘岭战役志愿军45师烈士遗照一一照片由原志愿军45师前线指挥所秘书谢万丁捐献,现被中国军史博物馆永久收藏。他一直记得那天的光线。不是在战场,不是在坑道,是在军博那个大厅里,天窗斜下来一束光,打在谢万丁捧着照片的手上。那几张照片——小得惊人,黑白的,纸质已经发脆——是他从上甘岭带回来的。几十年了,他没跟人说过这些事。他也不是个多话的人。可那天他站在展台前,眼神发直,把照片递出去的时候,嘴角动了动,说了一句:“他们一直跟着我。”没人问是谁,其实不用问。照片里的人,都穿着一样的棉军装,有的闭着眼,有的还睁着半条缝,脸上泥点没擦干净,嘴角泛白。那是死后的颜色。照片洗得匆忙,也没人取景对焦,更多像是“留下个证”。他一个个记得名字。老李、王士根、小周……有几个,他送进坑道的时候还拍了下肩膀,说等仗一打完请他们喝酒。结果人是带回来了,不是坐火车回的,是抬着、背着,从高地上一步步往下拖。有个医务兵拍下这些照片的时候手在抖,说相纸快没了,得快。也许正因为快,没有摆拍,没有修饰,那几张照片看着就像还没死透。他说不清自己怎么保住这些东西的。连队撤得太急,文件能丢的都丢了,他把照片塞进贴身口袋,贴着肋骨绑了两层纱布。几十年没跟人提过。他说怕这些脸被人拿去做展板、做口号。他说他们不是英雄,他们是人。旗子的事跟照片是一起想起来的。上甘岭那块597.9高地,后来被炮弹削低了两米。就那一面战旗,插在主峰,打到最后像一张筛子。旗子是块红布改的,上头写着字,一开始能看清,后来全被烟熏黑了。但没人敢把它换掉,那时候说得清楚,旗要是倒了,阵地也就没了。有个新兵晚上起夜,看到旗子在风里哆嗦,以为是人影,拔枪就蹲地上瞄。后来他自己说起这事的时候还笑,说那时候神经紧绷到见个布片都想开枪。可这面旗最后还是被带下来了,血迹、泥土、弹孔全在,连上头的一小截烧焦边都留着。再后来,这面旗出现在2019年国庆的阅兵场上,跟着空降兵战车,从天安门前穿过。说实话,站在那旗前,很多人哭不出来。不是不感动,而是不知道该怎么感动。你得真的钻过坑道,拿铁锹挖过冻土,捂过战友的尸体,闻过炸弹炸翻尸体的味儿,你才知道那旗不是象征,是替人挡子弹挡过风的东西。1952年的十月,山里夜里冷得结冰,白天却能晒脱皮。美军那时候像疯了一样往山上砸炮,炮弹炸得山都塌了,塌完再填。那几天,战士们的耳朵是聋的,鼻子是哑的,眼睛被硝烟熏得通红。有的战士已经不能走了,硬是绑在阵地口边拿枪抵着地守。一口水都没有,有个连队试着化雪喝,结果雪里都是黑色的煤渣和炸出来的铁粉,喝了肚子一拧一拧地疼。有个人断了腿,被放在坑道深处。他知道自己活不成了,就拽着班长的衣角说,给我把子弹留够,我自己来。那天班长转头没说话,只把两排子弹全给他塞过去。他最后确实没麻烦别人,敌人进来时,他引爆了身上的手雷,连同身下那块地一块炸飞了。还有人记得黄继光。那场反冲突时候,打着打着前头卡住了,全连趴在地上进退不得。他从侧翼绕过去,手里没枪了,只有手榴弹和匕首。后来怎么扑过去的没人看见,只看到火力点突然哑了。冲上去的人说,他是扑过去用身体堵住的枪眼。那枪口有点黑,边上沾着血,没人敢多看。战斗持续了43天。白天打完,晚上清尸,尸体都不整,来不及。他们就是趁夜把死者捆上麻绳,从半山拖下来。半路还得防炮,有时候一炸,绳断了,尸体滚下山沟,要找得找到天亮。营长的命令是,“哪怕找不回人,也得带回他的枪”。上甘岭后来成了词,成了精神,成了口号。可对那些回来的人来说,它不是词,是习惯性耳鸣,是每次睡觉前的鼻血,是不能吃炒面的胃病,是梦里突然炸响的那声炮,是永远记得的脸和没来得及说的那句话。谢万丁把照片捐出去那天,没人鼓掌。他也不需要。他站了很久,看着展柜玻璃反出来的自己,白头发贴着太阳穴。他低声说,“都在这儿了。”然后他就走了。照片安静地躺着,旁边的介绍牌字不多,只写了“志愿军烈士遗照,捐赠人谢万丁,原志愿军第45师前线指挥所秘书”。有人路过看了一眼,再走。有人停下多看了几秒,皱着眉。再往里走,是那面战旗,红色褪成铁锈,弹孔成排,像旧伤口结了痂。外头风有点大,军博的门一开一合,光一下一下地打进来。旗子没动,像是等着什么人再来。